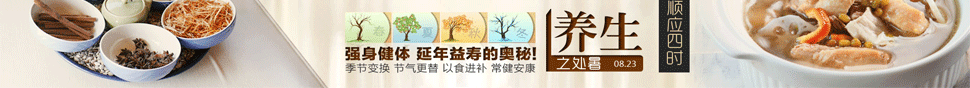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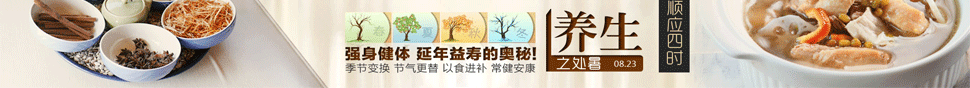
在大学用的最多的香水就是浪凡的紫霓裳,因为受到法语老师的影响,每次闻到这个香味就会联想起Michelle在课堂上唱玫瑰人生的场景,很很有故事和女人味。
后来喜欢上了菲拉格慕的shine,和一个朋友去西北大戈壁,她身上就是这种甜甜的花果香,佛手柑、小苍兰、白雪松木,肌肤被阳光包裹,就像瓶身斑斓的彩虹一样,可能跟西北的广袤无垠相冲突,这种阳光绚烂甜蜜的味道非常冲突,每次闻到还是会想起穿越敦煌的场景。所以我相信,味道是有记忆的。
这次旅行,也带了很多香水小样。
在甘南,最常喷的是柏林少女,简单的瓶身装着鲜血般妖艳的颜色,馥郁红莓掺杂粉胡椒的味道扑鼻而来,蜜感很重,后调广藿香和橡木苔不黏不腻非常厚重,心想,不就是我期待的甘南味道吗?激情和沉淀,带着它,想用这个味道记住这个地方。
寺庙桑烟
甘南之行是用寺庙串联起来的,记忆中的寺庙是烟雾缭绕的,而让我记住寺庙的,是一缕缕桑烟。
藏民喜欢煨桑。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桑烟。桑,是清洗、消除、祛除的意思,把柏树枝和香草堆砌在煨桑台,投入青稞炒面、酥油、曲拉和白糖,慢慢自燃,青烟袅袅上升,伴随一股酥油枯叶的味道,念经祭神,驱除灾难,祈求福报。
米拉日巴佛阁、郎木寺、拉卜楞寺,藏区的寺庙都修建得极为华丽,金顶斗拱,鎏金饰物,法轮、金盘、双鹿、覆莲、金幢经幡、套兽,阳光下光彩夺目。墙身是染红的萹蔴草,红黄相间的砖墙,点缀黑色门窗。色彩对比鲜明。蓝色为天,神秘高远,白色为云,圣洁祥瑞,红色为火,袈裟力量。绿色为水,生机活力,黄色为地,光明希望。
淡季的甘南只有我一个人,是个纯粹的看客。
虔诚的藏民,在桑烟笼罩庇佑下,一圈圈转着佛塔,在每一圈的结束会在台面上的算盘记个圈数。
磕长头,在寺庙门口原地磕长头的,绕着拉卜楞寺外圈磕长头的。
转经筒,在世界上最长的转经筒朝拜,走完一圈要3小时。
玛尼堆,他们坚信每个物体都是有生命的,包括石头,所以才会看到小石子在地上,就很珍惜得拾摞到一堆,这样就不会受人的践踏。
藏民在转圈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,他们可以对旁人熟视无睹,甚至站在旁边就是个打扰。嘴里念着六字真言,手上捻着佛珠,或是转着转经轮。寺庙里面念经学习的僧人。常年的跪拜大部分的藏民老人家腿脚都是不便利的,布满沧桑的脸庞,但是依然阻挡不住他们一日三餐般的礼佛朝拜。
我站在寺庙门口,有时站在山顶上,看着袅袅的桑烟上升,深吸一口气竟是如此的平静,但是无论在这里待多久,我都只是个局外人,他们血液里流淌的就是信仰,我无法感受,有时想偷偷懒妄想成为一个藏民,他们多么简单,放牧、吃饭、转塔。有时想奋斗的时候,觉得这种生活过一辈子就太无聊了。
羡慕他们,但是也不想成为他们。只是每每闻到桑烟的味道,就会想起他们执着的模样。
集市酥油
酥油是藏民生活的必需品,酥油茶,酥油饼、酥油灯···酥油满足了高原地区所需要的能量。酥油的味道,弥漫着整片藏区。
去到一个地方最喜欢的就是去逛当地的集市,在唐克镇,走过许多小店,因为风比较大,店铺都是用磁吸透明门帘与外面进行隔绝,同时不影响阳光照耀进来。无论外面多寒冷,里面都是很温暖的,也许就是这种温暖使酥油的味道更加厚重、浓烈、无法挥发。手工艺品店,绿松石手串、藏服、牛皮帽、蜜蜡,屋内陈设很陈旧,工艺品也像是百年前的古董。乐器店,六弦琴、胡琴、甲铃、锣、镲,挂在墙上、摆在货架上。杂货店,马用的马鞍、摩托车用的绑带、锅碗瓢盆等。无一不染上灰尘,带着时光的痕迹。
店铺的老板坐在角落,有些嘴里念着、手里转着,有些就着酥油茶吃糌粑,店里总有一股酥油味道,点着一盏酥油灯。我深深爱上了这种带点膻味的奶香味,像是从远古走来,没有经过进化,他们浸透了每件商品。
柏林少女没有派上用场,它被同化了。
我可能会在以后的某段时间,当闻到柏林少女的味道,会想起在甘南的旅行,但是一回忆起甘南,桑烟和酥油的味道就会扑鼻而来,原来,记忆和味道是相互的。因为足够深刻,所以不用刻意。
木子野老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guanghexianga.com/ghxyx/9498.html

